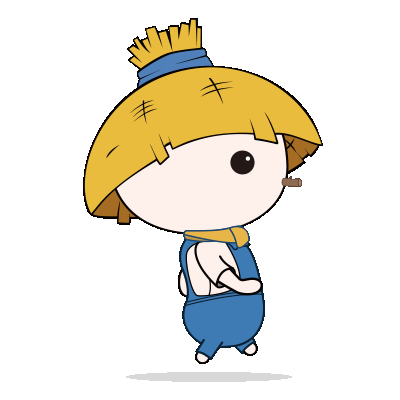干旱已经持续一千五百万年。
猿人走到了灭绝的边缘。
曾经遮天蔽日、漫无边际的雨林,被来自北方的冷冽寒风无情摧毁。
禾本科植物抓住机会,迅速填补了大地的空位。
粗糙、坚韧、难以消化的禾草,取代了嫩叶与果实。
无数植食动物就此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随后就是以它们为食的肉食动物。
旧有的生态系统轰然垮塌。
而这,只不过是这粒宇宙尘埃上发生过的众多大灭绝事件中,相对比较寻常的一起。
但对灵长类来说,却是灭顶之灾。
硕果仅存的森林,如同汪洋中的孤岛,彼此隔绝,并且还在不断萎缩。
为了能从一座沉没的孤岛逃往另一座孤岛,猿人们学会了依靠下肢行走——更准确地说,是那些不能直立行走的猿人,要么死在迁徙的路上,要么与森林同沉。
气候偶尔会反复,在有些时候——大概是几千或者几万年——空气变得,森林也再次出现。
伴随森林的复兴,猿人们也曾短暂地重振雄风。
但在千万年的跨度上,千年不过是一瞬。
总体来说,这颗星球始终在变得越来越干冷;猿人们的处境,也越来越绝望。
能够反刍的偶蹄目,一跃成为大地上最兴旺的族群。
可猿人没有尖牙和利爪,也没有能消化禾本科植物的四个胃。
它们依靠采集浆果、块茎和种子为生,但这些东西,也在其他动物的食谱上。
按照后世的标准,它们已经能够使用一些简单的打制石器。
但是猿人手里那些所谓的石器,充其量只是一些带棱角的石块,不足以让它们保护自己。
现在,连最后的森林都消失了,大地上只剩下一棵棵孤独的树。
树可以给猿人提供庇护,但树只是树,不是可以喂饱猿人的森林。
猿人要饿死了。
只是他们从未想过,那些与他们争夺草料的、千千万万吨肥美多汁的、徜徉在稀树草原上的偶蹄动物,也可以是他们的食物来源。
他们明明身处在丰饶之中,却要因饥馑而死。
趁着最后的天光,外出觅食的猿人们平安回到自己的树上。
为首的雄性猿人将一根只挂着几个可怜浆果的树枝,交给了一个没有出去觅食的雌性猿人——同时也是它的配偶。
严格来说,族群里的所有成年雌性猿人都是它的配偶,猿人们的小群体就是这样组织起来的。
猿人的配偶已有身孕,腹部明显鼓胀。但它之所以不出去觅食,不是因为怀孕,而是因为受了伤,无法行动。
猿人没有夫妻的概念,更没有优待孕妇的念头。
雄性猿人的配偶是它从另一个雄性猿人那里夺来的,它打跑了对方,然后杀死了对方的后代,好让对方的配偶可以尽快重新,为自己受孕。
而在雌性猿人时,它还会持续地殴打对方,以确保对方不会和其他雄配。
它没有道德上的善恶,它做这一切,都是被本能所驱使。
同样,本能也驱使它忍受饥饿,将那些本可以自己果腹的浆果,带给孕育着它的后代的配偶。
这究竟是爱,还是本能?
或者说,爱本来就是一种本能。
当晚,雌性猿人感受到一阵腹痛。
它发出尖叫。
它的同伴们却没有靠近,反而四散逃离。
至后半夜,雌性猿人产出了一具初见形状的胎儿。
它疲倦地依靠着树干,嘴角渗出鲜血。
其他猿人好奇地围过来,用手指轻轻戳动地上这团小肉球。
小肉球已经死了,死亡时间甚至早于它离开母亲的身体之前。
猿人们不知道,这团小肉球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因为它有一种特殊的能力。
在它之前的生命,不足以主动使用这种能力——或者说,还未触碰到生命的标准,就已经因此而亡。
而在它之后的生命,没有一个能比得过它。
但它的能力实在是太强大了。
强大到它只是刚刚有了那么一丁点意识的萌动,它就被它自己所杀死。
灵长类、哺乳纲、脊索动物,甚至有可能是自原初细胞在海底火山口的凝固熔岩中成型以来,这颗星球孕育的第一个施法者、同时也是最强大的施法者,在妊娠第四个月,死于自身能力的失控。
而类似的事情,还将发生很多很多次。
-----------------
不知过了多少年。
还是那片稀树草原,一个强壮的猿人伏低身体,借助枯草的掩护,悄悄向水塘爬去。
干旱仍在继续,但是猿人已经不再濒临灭绝,反而蒸蒸日上。
他们五个趾头的足迹,早已遍布在稀树草原的每个角落。
甚至,对于他们来说,这片温暖的大陆都已经有些拥挤。
一些猿人开始走出摇篮,向着更寒冷的土地进发。
比起他们的祖先,他们的被毛更加稀疏,而汗腺更加发达,配合更加强壮、修长的下肢,使得猿人变成一种自然界中十分罕见的擅于长途跋涉的动物。
这令他们成为了旷野之王。
在人科的一众生物中,他们是第一个真正掌握了直立行走的本领的亚种。
正因如此,后世的学者们,将他们称为“直立人”。
虽然直立人仍要与饥饿相伴,但是他们已经掌握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杀戮方式,那就是:
“掷石头”。
这个强壮的直立人已经接近到了足够杀死猎物的位置。
他的目标是一种四蹄、长角、体型巨大、集群行动的草食动物,此刻,后者正围聚在水塘旁边,啜饮着宝贵的泥水。
水源附近的杀戮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掠食者们都偏爱在水源附近发动攻击,但草食动物们依然会来到这里。
只不过,绝大部分掠食者捕杀的,都是族群中的老弱病残。
哪怕是长着尖牙剑齿的巨型猛兽,也不敢轻易挑战被捕食者中成年的个体。
但是这个直立人可以。
因为他很擅长掷石头。
四蹄、长角的动物们不是每天都会出现,所以这个直立人必须抓住机会,他先是找到了兽群中身型最庞大的个体,然后深吸一口气,舒展长臂,遵循着本能,将手中打磨的尖锐石块,全力向着目标掷了出去。
石头裹挟风雷之声,快到简直不可思议。
瞬间,猎物的左肩胛迸射出一股血雾。
下一秒,他的猎物突然拔足狂奔,然后所有四蹄、长角的动物都开始本能地跟着奔跑。
掷石的直立人迅速后退——即使是他,族群的首领,最强大的掷石者,也无法敌过万蹄践踏。
远处,他的同伴们飞快朝他跑来。
漫天烟尘中,直立人们背靠背,紧紧贴在一起,如同浪涛中的礁石,任凭蹄声如何恐怖,也纹丝不动。
奔逃中的四蹄、有角的动物绕过了他们。
掷石者的猎物没能撑太久,只跑出一小段距离,它就一头栽倒,抽搐了几下,很快就没了动静。
待到其他四蹄动物从惊慌中平静下来,直立人们才分散开,朝着猎物的尸体走去,他们挥舞手臂,喉咙里不断地发出低吼。
还活着的四蹄动物们默默离去,将同伴的尸体留给了旷野上最强大的捕食者们。
直立人们拿出工具,开始屠宰猎物。
他们所使用的工具,仍是打制的石器,但已经比猿人们手里的石头,要精致许多。
而且它足够坚固,已经使用了两百万年,还能再用一百万年。
作为首领,掷石的直立人,第一个品尝。
他掏出猎物的肝脏,大快朵颐,然后才轮到他的同伴们。
饱餐一顿后,猎人们把吃剩的猎物肢解,或挑或扛,全部带走——族群的老弱妇孺还在等待食物。
山洞内,年长的祖母听到了外出狩猎的子代、孙代们归巢的喧闹。
她将一些干枯的苔藓放入自己看护的石坑中,然后把手靠了上去。
不多时,一缕青烟从石坑中飘出,然后是更浓郁的黑烟,老母亲像呵护幼崽一样,轻轻向着石坑里吹气。
终于,火苗在坑底的灰烬升起。
围坐在石坑旁边的幼龄直立人们,无比敬畏地看着跃动的火焰,在得到老祖母的允许后,才怯生生地把手里的晒干的动物粪便放进石坑里。
火照亮了洞穴,也照亮了人的未来。
生火和丢石头。
释放能量与储存能量。
这两样本领,将帮助人类撑过永夏的暴晒、撑过无尽的严寒、撑过时光的淘洗,帮助人类渡过海洋、跨越陆地、扩张到这颗星球的每个角落,并最终帮助人类离开摇篮,航向无垠的星际。
-----------------
又不知过了多少年。
凯美特,黑土之地。
白城,灵魂之地,创世神之家。
深夜。
女人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在创世、工匠与艺术之神的神庙内回荡。
后殿沉重的大门外,法老正在等待。
殿内那个因婴儿胎位不正而承受巨大的痛苦的女性,是他的王后,也是他父亲的长女。
但是此刻法老最关心的,不是他遭遇难产的妻子兼姐姐——二人并无深厚感情,他们的结合也不是出于男女之爱;
相反,法老不仅厌憎他父亲的长女,还清楚知晓两人结合可能会造成的严重后果。
事实上,除了他父亲的长女,法老的后宫里还有大量的妃嫔,大部分时间,他都更愿意与他的妃子们过夜。
但他还是与他父亲的长女成了婚,并与后者交配。
他,他的父亲,以及黝黑之河两岸数不清的、曾经无比强大、如今却连名号都被遗忘的君王们,他们之所以要将自己的姐姐、妹妹乃至姑姑、女儿纳入后宫,不仅是因为没有凡人配得上王室之女,更因为,他们需要神力来统治。
为此,他们必须延续最纯净的天神之血。
而维持神血纯净的最极端的方式,就是让两个身负神血之人诞下后代。
所以法老们迎娶姐妹,一如“空气”与“雨水”、“大地”与“天空”、奥塞里斯与伊西斯、塞特与奈芙西斯的结合。
所以,法老此刻最关心的,是那个尚未出生的婴儿。
法老很确信,他的祖先曾如神明一般强大——不,准确来说,他的祖先就是神。
理论上来说,他也是神。
按照祭司们向民众宣扬的教谕,他不仅是神的后代,不仅是首席祭司,不仅是众神与凡间沟通的媒介,他还是神的化身,是行走在人间的神。
所以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他的话语,就是神的旨意,诸事皆可由他一言而决,万民皆以对待神明的方式,向他顶礼膜拜。
但法老很清楚,自己不是神。
因为他没有神力。
他没有,他的父亲也没有,他的兄弟姐妹们也没有。他的家族,已经很多年,没有再诞生过拥有神力的孩子。
现在,他们只是凡人。充其量,是有神的血统的凡人。
而凡人是不配统治众神之地的。
后殿内,似乎永远不会结束的尖叫,在冲上一个顶点后,戛然而止。
婴儿的哭啼随之响起。
法老立刻撞开大门。
“[上古伊普特语]男孩,我的主人,”一个老妪抱着一个皱缩、红紫的婴儿,跪在床榻边,讨好地望向主人,“[古伊普特语]一个男孩,一个健全的男孩。”
法老劈手从老奴怀里夺过婴儿,转身奔出后殿,甚至都没看床榻上的女人一眼。
神庙中央,七名祭司已在圣池旁恭候多时。
法老踏入混沌之水,将尚在啼哭的婴儿放在圣池中央冰冷的石台上,然后离开水池,向着祭司们点了下头。
待到水面恢复平静,七名祭司开始执行仪式。
他们齐声念诵,他们的喉咙里发出呜咽、悠扬的声音,不似人语,倒像是野兽的低吼。
法老紧盯着池水。
然而水面纹丝不动、平滑如镜。
直至仪式结束,圣池中也没有漾起半点波纹。
法老攥紧了拳头。
为了延续天神之血,他甚至与自己的异母姐姐媾和。
但即便如此,他仍然没能得到一个拥有神力的继承人。
神,究竟是由力量定义?还是由血统定义?
没有神力的神,还是神吗?
风吹过神庙的廊柱,发出又细又密的幽响,在法老听来,那声音,就像是奴隶们的喁喁私语。
王室家族失去了神力,但神血并没有就此断绝,拥有神力之人依然在不断出现,只是不降生在法老的后宫中。
这些流落民间的“神血”,或是被祭司们带走,或是被贵族们招揽。
流言已经开始涌现,人们说:王座上,只是一个冒牌货;真正的神,很快会将他取而代之。
祭司们毕恭毕敬地倒退着离开了圣池,可在法老眼中,他们的嘴角,分明挂着窃笑。
离开这间神庙,又有谁能想到,贵为神之化身的君王,只是一介凡人。
而这些服侍“神”的祭司,却能施展神力?
法老久久没有动作。
他的王朝会走向何方?
会像曾出现在这片土地上的所有王朝一样,伴随着神力的消失,而土崩瓦解吗?
婴儿的哭喊将法老从沉思中惊醒,这个可怜的小东西,因寒冷而痛苦,正在大声索要乳汁。
法老走入混沌之水,将他的孩子从石台上抱起。
望着后者皱缩的小脸,一种前所未有的情感在他的胸膛中被唤醒。
他将他的孩子小心翼翼地抱在怀里,用身体温暖着后者。
他向着后殿走去。
他必须改变这一切。
-----------------
又是数百年过去。
托里亚德半岛西岸。
阿开奥斯人对于特罗阿斯的都城持续多年的围攻,已经到了最后阶段。
阿开奥斯人中最勇猛者,捷足的英雄,带着满腔的怒火,驱策战车,孤身来到敌人的城门之前。
由佩里昂的梣木打造的长枪,在他的右肩怖人地晃动;比火光还闪亮的胸甲辉煌灿烂,如同初生的太阳。
“[上古迈坎尼语]出来!!!”他的咆哮甚至令诸神营造的城墙战栗,“[上古迈坎尼语]面对我!!!”
在地心海沿岸的诸城邦中,显露出特殊本领的孩童们,自幼就会得到更多的关注。
祭司们会把众神享用过后的祭品——蒙上双层油网炙烤的牲肉与内脏——献给他们。
因此,他们的发育潜力,得到了充分的释放。
比起同时代那些营养不良的普通人,他们普遍要高出一个头、甚至是两个头,身体也更加强壮。
行走在凡人间,他们奕奕如神明。
人们说,他们是多情的众神与凡人交欢后,留在人间的后代。
所以,人们称他们为——“半神”。
城门缓缓开启。
达尔达尼亚人中最善战者,头盔闪亮的驯马者,手提大盾、长枪,穿着同样闪亮的盔甲,大步走了出来。
驯马者的血脉,同样可以追溯到众神,但他并不是半神,他只是半神的后代。
事实上,阿开奥斯人的首领中,许多人并非半神。
虽然他们都有一个或是几个据说住在奥林帕斯山上的祖先,但是人们说,因为他们的血脉已经稀薄,所以神力也离他们而去。
不过,没有神力,不妨碍他们执掌权柄。
甚至阿开奥斯人的联军的统帅,这场战争的发起者,也不过是一个没有神力的凡人。
但从外表看,他们与半神无异。
事实证明,只要自幼摄入不输于半神的营养,人人都能长得和半神一样高大魁梧。
头盔闪亮的驯马者便是如此,人们都唤他“神样的英雄”。
不需再多说什么,双方就这样在城门外厮杀起来。
捷足的英雄率先投出他的铜尖梣木枪,那枪快如闪电;
但头盔闪亮的驯马者武艺高超,早在对方抬起手臂那一刻,就提前闪避,险而又险地躲过了半神的惊天一掷。
紧接着,驯马的英雄晃动着投出了他的长杆枪,正中敌人的盾牌,却被那绘着天空、大地与海洋的五层大盾弹开。
双方随即拔出佩剑,继续战斗。
城墙上的达尔达诺斯人与城墙下的阿开奥斯人情不自禁地屏住呼吸,无不看得目眩神迷。
事前谁也不曾想到,一介凡人竟能与最强大的半神打得有来有回。
但是神样的英雄,最终还是没能战胜半神。
捷足英雄的利刃,贯穿了驯马者的喉甲,戳断了后者的脖颈。
半神赢得了决斗,手刃了他的仇敌,可他的怒火,却没有因此平息,反而愈发炽烈。
他割开对手的筋腱,将对手的尸体系上战车,绕城拖行三周,让对手的头颅在尘埃中翻滚,然后才返回营地。
他的母亲曾告诉他:“若你前去,你必将名垂千古;可是,你也将命不久矣。”
“来吧,”他想,“我准备好了。”
-----------------
数百年之后,在极东的遥远土地上,又一场旷世大战即将打响。
二月,甲子,清晨。
经历艰难的跋涉,名为“发”的周人首领,终于率领他的西土联军,依约抵达了殷郊牧野。
而他的敌人——商王的大军,已等待多时。
大战在即,西土联军中,来自蜀地的巴人战士们,在两军阵前跳起了战舞。
随后,来自姜戎部落,名为“尚”,担任“师”职,被“发”尊为“父”的中年炼气士,策动战车,率先出阵。
周人的百夫部队紧随其后。
“尚”如同俯冲的雄鹰,锐不可当,直接凿进商人的战阵,长戈所向,血肉横飞,搅乱敌军战线后,又透阵而出,折返回来。
见师尚父成功“致师”,西土联军士气大振。
“发”左手执黄钺,右手持白色牦牛尾之节,乘坐战车,在西土联军阵前检阅。
检阅完毕周人与盟友的部队后,“发”高声道:
“[古赛里斯语]友邦的国君们!治事的大臣们!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们,以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国的人们!
“[古赛里斯语]举起你们的戈,排列好你们的盾,竖立起你们的长矛,听我的誓词!
“[古赛里斯语]古人说:‘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
“[古赛里斯语]如今,帝辛只听信妇人的话,对祖先的祭祀不闻不问,废弃同祖兄弟而不任用,却对从四方罪犯推崇尊敬,让他们施残暴于百姓,违法作乱于商邑,使他们残害百姓;
“[古赛里斯语]现在,我奉天命进行惩讨。”
宣告敌人的罪恶后,“发”开始申明作战纪律:
“[古赛里斯语]今天的决战,我们进攻的阵列的前后距离,不得超过六步、七步,要保持整齐,不得拖拉;
“[古赛里斯语]在交战不超过四、五回合,六、七回合,就要停下来,整顿阵容;
“[古赛里斯语]奋勇向前啊!将士们!望你们威武雄壮,如虎如貔、如熊如罴!
“[古赛里斯语]前进吧,向商都的郊外!不要攻击制服从敌方奔来投降的人,要用他们为我们而战!”
誓词的最后,“发”特意强调,“[古赛里斯语]不要畏惧商人的‘贞人’、‘鬼巫’和‘众子’!要勇敢地与他们战斗!如果今天我们不奋力向前,我们自己就会被杀!”
誓毕,开战。
这一战,天昏地暗、血流漂橹,从早上,一直厮杀到晚上。
在数万乃至十数万人规模的大战场上,炼气士完全失去了一锤定音的能力。
“发”不是炼气士,他绝大部分的部众和盟友,同样不是炼气士。
但他们却战胜了以炼气士为主要战力的殷人。
纪律、组织和自我牺牲,压倒了个人武力。
哪怕是最强大的“贞人”、“巫”和“子”,在牧野之战这等前所未有的大战中,也耗尽了气力,被最普通的长矛戳死。
最终,商人战败,商王帝辛逃入朝歌,以玉覆面,自焚而死。
次日,“发”入朝歌,于战车上,向帝辛射箭三次,以轻吕剑击帝辛之尸,又以黄钺斩帝辛首级,悬于大白军旗之上。
随后,“发”训诫殷民,威命明罚,又遣师尚父追讨残敌。
战后第四日,师尚父得胜归来,献俘虏、首级。
战后第五日,“发”薪祭上天、周人先王、殷人鬼神,于朝歌立政。
人类是一种奇妙的生物,相比起这颗星球上的其他群居动物,他们能组织起更加庞大的群体。
而且,群体里的个体越多,他们就能创造出越多的东西。
最终,人被他们的创造物所托举。
王权取代了神权,凡人战胜了神子。
神帝的时代结束了,人王的时代就此开启。
-----------------
多年过去,在季风大陆,又一名王子呱呱落地。
祭官们循例检验王子是否有资格成为“波拉乎曼”。
然而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当王子的父亲闯入祭坛时,他惊讶地发现,祭官们全部七窍流血,昏迷不醒。
传言很快扩散开去。
人们说,王子降生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踏四方土地,言:
“天上地下,唯我独尊。”
-----------------
又是多年过去,黑土之地的王朝已经不知更替了多少轮。
在离黑土之地不远的地方,山与海之间的一座山谷里,一个来自远方的年轻人,找到了那个传说中的青年。
“[古伊地语]他们说,”年轻人沙哑地问,“[古伊地语]你用五张饼、两条鱼就喂饱了所有人。”
“[古伊地语]他们还说,我能在水上走,”青年笑了,那笑容平和,令人不自觉想要亲近,“[古伊地语]有什么我能为你做的吗?”
年轻人扯开衣袖,露出手臂上令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可怖增生物。
青年却不感到害怕,他让年轻人坐下,仔细检查过,说,“[古伊地语]我也没有见过这种东西,不过,我可以试试。”
“[古伊地语]怎么试?”
“[古伊地语]把这块肉完整地挖掉,再让被挖掉的地方恢复。你会承受巨大的痛苦,而且,我也不知道,恢复的究竟是这块增生物,还是你原本的手臂。”
“[古伊地语]有什么办法就来吧,”年轻人惨然一笑,“[古伊地语]我还有得选吗?”
“[古伊地语]会很疼,要忍住,”青年为年轻人倒了一杯酒,“[古伊地语]喝下它,或许能对你有点帮助”
年轻人低头望向酒杯,酒中之酒殷红如血。后来,人们说,那就是青年的血。
年轻人将酒一饮而尽,点了点头。
青年递给年轻人一团亚麻布,让后者咬着。
“[古伊地语]我只要你做一件事,”青年说。
“[古伊地语]什么?”
“[古伊地语]相信我。”
刀子割开血肉,惨叫声响彻山谷。
年轻人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失去意识的,但当他醒转的时候,天才刚刚亮,可他明明记得,他是下午来的。
他掀开衣服,那丑陋、可怖的增生物已经消失了,新生的皮肤,如婴儿般细腻。
他跌跌撞撞爬出草棚,失血令他头晕眼花,没走出几步,他就摔倒在路上。
青年的一个追随者发现了他,将他搀扶起来。
“[古伊地语]带我去见他,”年轻人说。
在山顶,年轻人见到了青年,后者正在看日出。
见年轻人过来,青年望向他。
“[古伊地语]怎么了?”青年问。
年轻人的眼泪夺眶而出,“[古伊地语]救主,请允许我追随你。”
“[古伊地语]那就来吧,”青年看向山谷中,扎着帐篷等待救治的穷人,“[古伊地语]我用得上你。”
-----------------
又是多年过去,遥远的东方,曾经周人与殷人交战的土地上,下起了滂沱大雨。
暴雨中,头裹黄巾的信众,正在与前来讨伐他们的官军交战。
信众据城而守,而且人数远多于官军,本应占据优势。
可他们缺少军械铠甲,训练也不足,反倒是被人数更少的官军攻上了城墙。
局势对头裹黄巾的信众们越来越不利,官军已经在城头站稳了阵脚,并开始一点点将信众从城墙上逐下。
斩木为兵,可木终究不如兵;揭竿为旗,可竿始终不是旗。
城破在即,绝望与悲愤在信众中蔓延。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最后的呐喊在各处响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
城门上方,战斗最激烈处。
身负重伤的渠帅被信众们拼死救下,但已经晚了,一柄铁剑从他的右胸刺入,由后背透出。
渠帅已经能感觉到,自己的生命,正在一点点被抽离。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远处隐约传来信众们的呐喊,“苍天已死,黄天当立。”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渠帅惨笑着念诵,“苍天已死,黄天当立。”
金铁交击之声就在耳畔,官军已经杀至身前。
头裹黄巾的信众们拼死抵抗,却无济于事,他们一个又一个地倒下,死不瞑目。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渠帅握住胸前的铁剑,颤抖着念诵,“苍天已死,黄天当立。”
在身旁信众的惊呼和阻拦中,渠帅猛地拔出插入自己胸膛的铁剑。
“黄天!!!”他凄厉的呼号传遍城池,“黄天!!!”
城头,原本还在忘我厮杀的士兵们听到这声音,先是一滞,旋即纷纷仓皇向远处逃去,甚至都不顾上身旁的死敌。
因为罡雷,可是不分敌我的。
天威之下,形神俱灭。
战场上,唯有渠帅一人高举铁剑,孤身挺立。
一道霹雳自九霄落下,所有人只觉眼前一白,过了好一阵,才听到“轰隆隆”的巨响。
等到信众们的视力恢复后,官军已经退却。
信众们瑟缩地爬上城头,只看到了遍地焦黑、蜷缩的尸体。
-----------------
又是很多年以后,在北方,遥远的北方。
三男一女正在亡命奔逃。
他们拼命抽打胯下的战马,只求能将追兵多甩开一点距离。
行至一棵大树旁,其中一个男人终于支撑不住,一头摔下马来。
他的伙伴们见状,急忙回救。
他们将重伤的男人扶到树旁,让他背靠大树坐着。
“[古尼尔语]走吧,你们,别管我了,”重伤的男人已经油尽灯枯,却仍面带笑意,“[古尼尔语]我要去见众神之父了。”
“[古尼尔语]闭嘴,”为首的男人呵斥前者,转头对女人说,“[古尼尔语]治好他。”
“[古尼尔语]别白费力气了,”重伤的男人剧烈地咳嗽着,“[古尼尔语]那些家伙留的伤,治不好的。”
同伴们默然,因为他们都能看到,重伤男人的左肩,已经扭曲成了一个骇人的形状。
而这只不过是最明显的伤,除了肩膀,还有肋骨、膝盖、手肘……
他们强大的自愈力,如今却是一种诅咒,骨头折断后,如果没有被正确拼接,就会是这种后果。
他们的敌人不仅发现了这一点,还高效地利用了这一点。
重伤的男人喘着粗气,“[古尼尔语]把我绑在树上,让我站直,我不可手中无兵器而死。”
另外两人看向首领,为首的男人点了点头。
“[古尼尔语]再见了,兄弟,姐妹,”重伤的男人笑着,“[古尼尔语]我们在万神殿,再相聚。”
等革新修会的修士们追到此处时,重伤的男人早已死去。
修士们下了马,来到大树旁,静静伫立。
人们说,这些北境的半神们,无不处于永恒的狂怒之中。
人们说,他们会痛饮蜜酒,然后化身为熊,在战场上掀起腥风血雨。
但此刻,这名死去的战士,面容无比安详。
没有人比革新修会的修士们,更了解这些“披熊皮者”。
他们与他们战斗了几代人,他们熟悉他们,就像熟悉自己的朋友。
只有他们才知道他们有多勇敢,只有他们才知道他们有多忠诚,才知道他们有多难杀死。
为首的修士走上前,将圣徽贴近死者的额头,想要为后者的灵魂祷告。
但想了想,修士终究没有这么做,他决定让这个勇士以异教徒的身份安眠。
就在这时,刺耳的呵叱从修士们背后传来。
“你在干什么?!扫罗?!”
德戈特枢机——宗座的眼睛和舌头——来了。
扫罗没有说什么,只是收起了圣徽。
“烧掉尸体!挫骨扬灰!”枢机司铎颐指气使,喝令道,“把这树也给我砍倒!一起烧掉!异教徒的东西,一样也不许留下!”
革新修会的修士们默默听着。
如果异教徒东西,全都要被清除掉;
那么修习过异教神术的修士们,又会面临什么样的命运?
-----------------
十几年之后,塞纳斯海湾,山前地。
战火再次燃起,皇帝御驾出征,亲自前来讨伐两山狭地的叛逆。
而这一次,山前地武装到了牙齿,遍地是设防的城镇。那些没有堑壕和炮垒保护的城镇,也在加紧施工。
哪怕是倾全帝国之力,也不可能啃下已经完全堡垒化的低地。
皇帝必须另觅他法。
深夜。
一间狭窄的卧房里。
一个身着仆人衣服的男人,正与另一个身着军服的男人对峙。
“你不敢,我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不起眼的仆人打扮的男人像是在自我催眠,他咬牙切齿重复,“但是你不敢!你绝对不敢!”
身着军服的男人只是轻蔑地笑了一下,然后松开了手。
特制的松发引信被启动。
烈焰和冲击波毁灭了房间里的一切。
不仅毁灭了两人的生命,也毁灭了这场对峙发生过的证据。
没人知道,主权战争期间,究竟有多少宫廷法师被杀死。
也没有人知道,有多少塞纳斯人,在无人见证的情况下,做出了多么勇敢、多么伟大的牺牲。
-----------------
[现在]
一辆来自圭土城的马车和一辆来自永恒之城的马车,正在从不同的方向,前往新垦地。
但是车上的人目标一致。
他们都要找温特斯·蒙塔涅。\r\u2029
\u2029[贺新郎·读史]
\u2029
[MZD]
\u2029
[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u2029
[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蹻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
\u2029
[大仲马说,历史是挂小说的钉子;席德·梅尔说,玩家和游戏设计师是邪恶的同盟]
\u2029
[笔者觉得,读者和作者同样是邪恶同盟,读者要放弃很多常识、很多理性,去相信作者描绘的世界是真实的、勾勒的故事是可信的,这是非常大的牺牲]
\u2029
[相应的,作者一方面要忠于自己所讲述的故事,另一方面也需要重视读者的付出]
\u2029
[作为一名读者,笔者并不喜欢给人类发家史找拐棍的想法,譬如外星人、魔法、上古种族。因为真正的人类文明没有外星人和魔法的帮助,一群猿猴仅凭自己走到了今天,毫无疑问,自强不息的人类更伟大]
\u2029
[但作为一名作者,我希望自己的小说能挂在名叫历史的钉子上,这样的话,这个故事可以,更有沉浸感]
\u2029
[其实作者走出幕后发言,已经破坏了沉浸感,所以请原谅我小小打破一次盟约,也请相信,我永远是你们忠实的邪恶盟友]
\u2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