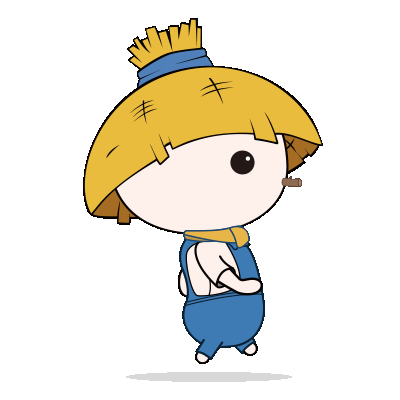看着祁昭浅昏过去,动手的人也慢慢松了些许力道。
他们抬头看了一眼云予薄,但云予薄只是皱着眉,没有给他们命令,他们也不敢停。
祁昭浅穿的是黑衣,看不出血液浸染得如何,但地上都是小摊小摊的血,难免让人心悸。
她虽是陛下,可身旁无一人,没有一兵一卒,也没有一点权利,很多人只会听从云予薄的命令。
医者仁心,最终是荼箐站出来说话,打破这凝重且奇怪的氛围。
“帝师,不能再打了,陛下昏死过去了!而且,再这样下去的话,这双腿就真的保不住了。”
她出声制止,云予薄看着凳子上只有轻微呼吸证明活着的人,终是松口。
“罢了,到此为止,送回抚云殿,荼箐,你负责照顾好。”
云予薄喝了一口茶,语气中并不关切祁昭浅是死是活,只是把任务交待给荼箐。
有荼箐在,祁昭浅不可能死,况且,她的意思也很明显,让荼箐负责医治祁昭浅。
“是。”
荼箐点头应下,得令的人停手,她赶忙上前查看祁昭浅伤势,表情有些凝重。
她摸到一手的,给祁昭浅喂了点药后用手小心翼翼的探查那些骨头和伤口。
云予薄让她负责,她自然要尽心尽力。
“还好,没有内伤,都只是皮外伤,应没什么大碍,但外伤难愈,可能两三个月都站不起来……”
她说给云予薄听,云予薄垂眼沉思了许久,侧头吩咐道:“通知各位大臣,陛下身体有恙,什么时候身子好转,什么时候再上朝,近几日的重要事,写成奏折上报便可。”
云予薄吩咐完,眼神落到祁昭浅身上。
她给过机会了,在她这里,没有一而再再而三的道理,事不过三,但凡祁昭浅没有那么犟,也不会落得如此局面。
但云予薄也有往好的方面想,祁昭浅能分析准确局势和实践着逃跑,倒也还能夸上一句勇气可嘉和聪明。
但这份心思将会被永远扼杀,让她无法再敢起。
荼箐命令着些许侍从抬着祁昭浅离开,切记路上小心,放她到床上的时候也务必小心,千万千万不要碰到伤口。
祁昭浅被送走,云予薄慢慢站了起来,看着现在一片狼藉的场面。
她看着那些血,想着刚刚祁昭浅反抗发怒的模样,心里没来由的一阵烦躁。
云予薄侧头看了看自已被祁昭浅伤的伤口。
已经没有再流血,但是触感尚存,有些麻,有些疼,顺便心中有些不爽。
祁昭浅速度太快,众人没想到她会如此做,云予薄自然也没想到。
云予薄叹了一口气,慢慢转身打算离开。
荼箐察觉到她的目光和动作,想着是不是她伤口痛了,便赶忙跟上去。
“帝师,你的伤……下官一会儿来为你处理吧。”
她提议着,云予薄却摇了摇头。
“不必,将药膏给我,我自已来便好,你先处理她的伤,可别让她残了,荼箐,你下次还是小心谨慎些为好,这次的过失我并便不追究你。”
云予薄说着,拿走了她手中的金疮药。
荼箐一愣,看着空荡荡的手心,有些不放心的开口。
“帝师确定自已来吗?这药有些痛,但效果极好,帝师用时忍耐些许。”
她叮嘱着,云予薄皱眉,但未曾再说些什么,只轻轻嗯了一声,大步离开。
云予薄回了屋子,褪去衣衫后一点一点把伤口擦拭干净,随后上药。
药撒在伤口上,钻心的疼痛传来。
她微微皱眉,闭上眼睛去感受那抹痛。
还好,皮外伤而已,并不算什么……
祁昭浅昏迷了三天,这三天里,她有些时候会有意识,但有些时候,又陷入梦境,不愿醒来。
她能听到有人在自已耳边窃窃私语,想睁眼但是都睁不开,她想动一动,想翻身,可是哪里都没有知觉,只要稍微用力些,便会刺痛难忍。
腿……断了吗?
她不禁想哭,梦中的她嚎啕着,哭得厉害,而现实却是眼角落下几滴晶莹泪珠,小声呜呜咽咽。
这是祁昭浅过得最难受的一个冬日,醒来之后,看着被木板和布条包裹缠绕着的腿,她心如死灰。
云予薄为控制她,还掰开了她的嘴,给她喂了毒药,以此来威胁她。
那晚的她腹痛难忍,额头都是冷汗却又动弹不得,痛苦异常。
云予薄坐在她床边,居高临下的看着她,伸手拨开她被汗水浸透的发丝,如同恶魔一般缓缓低喃。
“若还有逃跑的心思,凡你踏出宫门一寸,便会肝肠寸断为泥,生生折磨你七日,尸虫爬满全身才会让你断气,陛下,听话些可好?”
祁昭浅被吓得不敢开口,侧头躲避她的触碰,眼中都是因为疼痛泛起的泪水。
她心中怨恨反抗,不愿开口,不愿喝药,不同任何人说话。
但在听到荼箐的劝告时,又只得乖乖张嘴。
“陛下,不好好上药和吃饭的话,这双腿可能一辈子都站不起来……只能坐着,躺着,不能跑,不能跳。”
荼箐给她的腿一边上药,一边开口叮嘱,同她说了很多。
祁昭浅咽了咽口水,不想自已变成个瘸子,只能乖巧听话,老老实实的养伤。
前一个月,她只能躺在床上,很是受限。
但云予薄也没放松对她的教导,她躺着也要她学,要她读书识字。
祁昭浅偶尔会胆怯的看上一眼窗外之景,又快速回神,将心思用在书本之上。
第二个月,她终于可以坐起来,但不能走动,荼箐会用椅车推着她出去走上一圈,让她呼吸呼吸新鲜空气,那是她最期待的时候。
待到熬过了那个冬日,她才算是真真正正的站了起来,又花了一个月才痊愈……
往事在脑海中不断上演,那些的回忆疼痛清晰,她这才下意识的往后躲去,躲避她的触碰。
云予薄有些不悦,冷声开口。
“别动。”
祁昭浅不敢再躲,只抬眼看着她,有些怯。
云予薄用手绢轻轻将她嘴角擦干净,动作虽不温柔,但也不粗鲁,比起她以前可好上了太多。
好像自长大以后,云予薄便很少再动手打她,而这顿鞭子,是她太过放肆惹的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