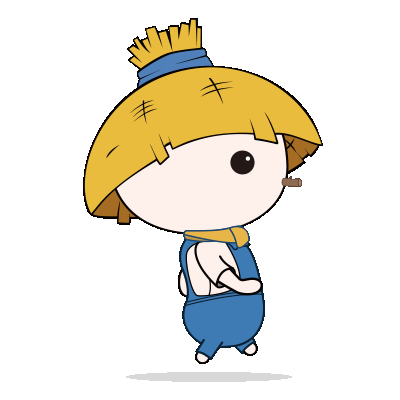她隐约可以看到床榻上祁昭浅的身影,趴在那没有任何反应,看样子睡得很熟。
云予薄的动作很轻,虽然知晓自已不是做贼,但内心中还是希望自已不吵醒祁昭浅,也不想祁昭浅知晓自已今夜来过。
她走了进去,抬眼朝书案看,一眼便看见了自已因为着急而遗落的书。
书籍位置没有发生任何偏移和变化,未曾被人动过。
她慢慢走过去拿起,再三检查确认之后,转身打算直接离开。
云予薄心中默默想着祁昭浅倒是称得上乖巧,只要是自已的东西,祁昭浅都不会乱动,她也没有那个胆子乱动。
但她也明白,祁昭浅只是表面上没有胆子,可心底里一直窥探着她,胆大包天。
云予薄不是一个拖沓的人,任何事都喜欢速战速决,但也不缺乏犹豫不决的时候,她会权衡利弊一切,选择对自已最有益的……不过那种情况基本很少出现。
“帝师……”
云予薄抬脚欲走,身后忽然传来祁昭浅的低喃。
很轻微,但在寂静的夜中,听得真切,也显得格外清晰。
云予薄的身子僵住,空气凝固起来,思索自已是不是声音太大吵醒她了,要不要回头解释一番。
但她下一秒便否决了自已的想法。
醒了便醒了……跟一个棋子有何好解释的。
她定了定心神,慢慢回过头去,准备迎接祁昭浅是注视。
云予薄甚至可以想到祁昭浅那不解疑惑的神情。
但想象中的画面并没有到来,他转过身去后,床榻上的人没有任何动作,也没有任何多余的话语。
云予薄微微皱眉,不禁疑惑起来。
莫非是自已刚刚听错了?
亦或者梦话吗?怎么梦里唤她?还是说已经醒了看见她了?
云予薄咽了咽口水,慢慢朝着床榻走近,探寻自已想要寻求的答案。
若是醒了,她解释一番便好,祁昭浅也不会多想多说,不解释也行,祁昭浅也没有那个胆子问。
她一步步朝前走着,待到看清眼前的一幕,云予薄直愣愣的站在原地,不淡定了。
她看着祁昭浅怀中的东西,眼睛里都是问号,祁昭浅怀中抱着的,怎么那么眼熟?
云予薄侧头,看着本该挂衣服却空着的地方,心中又在咒骂祁昭浅疯了。
她看着眼前人,再三确认祁昭浅怀中抱的衣衫是不是今天她给自已披上的那一件。
她希望不是,但是事实已经摆在了眼前,昭告着祁昭浅那没有藏住的小心思。
少女脸上未施粉黛,明眸轻阖着,肌肤白皙娇媚,烛火映照下,让人忍不住多看两眼。
不知她梦里梦见了什么,双颊红润,脸上都是恬静和满足的笑。
“帝师……”
在云予薄发愣的功夫里,祁昭浅又像小猫一样轻轻的说了一句,语气软绵似撒娇。
她还无意识的蹭着那衣衫,搂的更紧了些,就好像抱着的不是衣服,而是云予薄本人,把自已藏着的情绪借着宣泄。
云予薄抿唇看着这一切,手中的书都被她无意识的捏皱。
祁昭浅大概是没有想到她今夜会来,才如此肆无忌惮,贪恋那一抹压根不存在的温存。
这语气同平日里祁昭浅唤她时不一样,今夜这些呼唤话语中有缠绵,夹杂着眷恋,傻子都知道藏着什么。
被祁昭浅这几句话这么一搞,云予薄呼吸一滞,心中一慌。
不过是她披过的一件衣衫而已……祁昭浅居然趁她走后抱着睡,还一脸的恬静与欢喜。
她觉得这样太过荒谬,伸手想要将那衣衫扯出来。
但手伸到一半,她停止了动作。
不行……这样的话,祁昭浅必然会醒来。
若是醒来,她大可以一脸不高兴的质问祁昭浅这是在做什么,但……罢了。
云予薄往后退了一步,心中思绪万千。
自她回来,祁昭浅每日都能给她惊吓,让她拿不出应对之策。
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 祁昭浅就把心思打到了她身上,拙劣的藏匿着。
而她,一直没有太过细究,最近才发现……
云予薄眼中闪过迷茫和不解,但最终都被狠厉掩盖。
她在心中安慰自已不碍事,三个月之后祁昭浅及笄礼完成,侍君选出,祁昭浅的心思必然会从她身上撤下,转移到那些侍君身上。
毕竟那种时候,她的身旁有更多的人相伴,不会只有她一个。
云予薄眼中怀疑,祁昭浅是因为一直被困在宫中,从而产生这种畸形的眷恋。
许是察觉到自已身旁有人盯着自已,祁昭浅不太舒服的蹙眉,她的睫毛颤了颤,有要醒的趋势。
云予薄有些紧张,但还是故作镇定站在那,观察了一会。
还好,祁昭浅只是微微蹙眉,并没有睁眼,但搂着外衫的手还是很用力,像是宝贝,谁也不可能抢走。
云予薄叹了一口气,强迫自已转身,她走出祁昭浅的寝殿门,在门口站了一会。
凉风打在她身上,让她清明不少,一如既往的坚定自已的想法。
她将门关上,刚刚的画面在脑海中挥之不去。
祁昭浅年少,藏不住心事,藏不住喜悦,藏不住贪恋。
云予薄动摇过,但这么多年,她永远都只把她当做棋子看待,就算祁昭浅如此,她也只当做没看见。
云予薄叹气,回自已寝宫的路上她走得飞快,好像在逃避什么。
天空不知何时被乌云遮蔽,星月隐藏了行迹,在这墨色的夜里,有人沦陷,有人清醒。
第二天一早,祁昭浅缓缓睁开了眼。
她先是看了看书案,又看了看手中的衣衫。
昨夜好梦,她睡得舒坦,梦中繁花似锦,安宁快活,她自由自在,无拘无束。
不过书不见了,看样子云予薄来过。
何时来的?会不会看见她抱着这衣衫……
祁昭浅心中莫名有些紧张,她默默爬起来,把手中的外披挂回了原处,营造出一种从未被动过的假象后又躺回了床上。
她一直看着那衣衫,脑子里都是昨夜的梦,直至宫女进屋给她梳洗,才恋恋不舍的收回了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