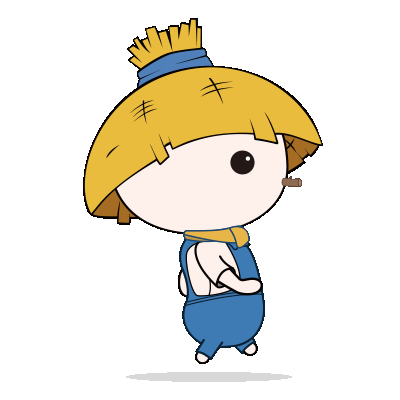许久都没有再传来一丝半点的声音。
整个楼梯口一时间内安静的可怕。
温言喻眸色微变,站起身,刚要下楼查看。
楼梯口再次传来了交谈声。
温言喻仔细辨别。
是傅寒川的声音。
没了刚刚争锋相对的戾气,相反,是一种沙哑到几乎破裂的气音。
温言喻心头一跳。
发生什么了。
冰冷月光落在走道尽头。
[在轮回里我燃烧了40多年,剩下30年在言言身上,还有3年多在你身上。]付知言神色平静:[我还有21天。]
[21天之后,这个世界上……所有世界中,不会再有我的存在,你也不用介意我和你抢夺地位了。]
象征着真相的惊雷与窗外雨声一同落下。
傅寒川眼底情绪猛的一颤,骤然僵在原地,呼吸在这一刻戛然而止,仿佛时间也被定格了。
眼中的怒气慢慢凝滞,消散,取而代之的是巨大的错愕,迷茫,无措。
原本的火气和困惑瞬间被冷水熄灭。
没了升起的力气。
也不知到底是他们是一个人这件事,还是忽然得知自已只剩3年寿命这件事。
哪个带来的冲击更大。
付知言不紧不慢的解释清楚了目前的状况。
傅寒川表情空茫了好半晌。
[我知道要接受自已只剩三年的寿命这件事很困难,但这是事实,你的身体应该已经开始出现异常了,那些东西原本来在我身上,但因为我正在消散,所以它们没了压制,开始向你侵蚀,那是燃烧寿命的副作用。]
付知言声音的平淡:[你觉得我自私的代替了你做出决定也好,或是觉得不公也好,这是已经无法改变的事实。]
[但我们是一个人,言言爱上的自始至终都是同一个人,你爱着言言,我也同样。]
[很抱歉,没有通知你一声,但我只有这个办法。]付知言平静的说着。
[我只是个普通人,在那百年里也不曾有过改变,只是多了一层需要同等代价的力量,我没有移山倒海的本事。]
[这已经是我能找到的,最好的办法了。]
付知言没有和傅寒川对视,而是转头看向窗外明月,光落入他的眼中。
自带死气色调的一双灰眸在夜色下并不显得悲伤,反而带了些许温情。
傅寒川沉默着。
付知言同样。
一片死寂中。
傅寒川攥着拳,捂住了通红的眼,他能感觉到自已的手正在剧烈的颤抖着,甚至能听见身体内部神经崩裂的声音。
他想要让自已把付知言这些话当成谎言。
他在想自已该是抓住对方的衣领,把对方往死里揍一顿,怒骂他凭什么代替自已做下决定,凭什么要让自已去死。
还是骂对方是个骗子,这一切都是假的。
可稍一细想身体上的异常,手腕处同样的黑痕,
他骗不了自已。
他的眼中泛起一股说不上来的情绪,也许是恨,也许是不敢置信,又或许是不甘。
一阵死寂的沉默后。
傅寒川缓缓开口,没有声嘶力竭的追问,也没有愤怒的火气。
只有一句仿佛被抽干了所有力气的质问。
[言言怎么办?]
傅寒川开了口。
付知言微微皱眉,没明白。
傅寒川吞咽下喉咙中的苦涩,沙哑着声音质问:[言言一个人该怎么办?]
[他照顾不好自已的。]
[他的身体……才,刚刚好起来一点,如果不说,他平时连吃药都会忘,发烧都意识不到,他只有一个人,他对交际一窍不通,那么多人惦记他,要是被欺负了,怎么办。]
[我不在了,言言该怎么办。]
[他该怎么办。]
傅寒川表情颓然,没有过多其他情绪,甚至没有看向他所质问的当事人,只是反复重复着这句问话。
声音又低又哑,像是一点一点从喉咙中挤出来的,费劲了全身的力气。
干涩到有些发颤。
付知言沉默的站在那,静静看着对方犹如困兽,一遍遍自问那些,他也曾质问过自已无数次的问题。
许久。
傅寒川放下了手,问他:[只要那个叫君常墨的东西不死,言言就还会有被抓走的危险,对吗。]
付知言沉默着点头。
傅寒川抬眼望向夜色,嘴唇翕动着,是入骨的苦意:[我答应过,会让他幸福的。]
[医院开的药副作用大,他每天晚上,不是在失眠,就是在做噩梦,晚上他经常被吓醒,他以为我不知道,就窝在我怀里撒娇,可他抖的那么厉害,我怎么可能不知道。]
[我不在他身边的时候,他一被吓醒,就会去房间衣柜里缩着,一直等到我回家,装作什么也没有,出来找我,浑身都是冷汗。]
傅寒川一字一句说着,握拳的手在颤抖,后知后觉的钝痛蔓延了全身。
[他和个呆子一样,那么傻,难受了也不知道说,甚至不知道自已在被欺负,很多事情我都没来得及教他,他肯定会被人欺负的。]
[他才刚刚好起来一点,三年时间怎么够。]
大滴大滴的泪水溢出眼眶。
傅寒川不停做着深呼吸,试图平稳下情绪。
眼前似有大片光污染在闪烁,世界在眼中无声崩溃,嗓音沙哑哽咽到几乎已经听不清自已在讲什么了。
付知言垂着眼,很低地回了声:[对不起,我没有其他办法了。]
三年后,他死去之后,他的灵魂与本源会被碎化进入屏障,而他与那位造物主交易时残留的东西会与他为中介,牢牢黏附在屏障之上。
他本就是这个世界的灵魂,从外界来看,不会看出任何异常,但只要君常墨再次靠近这个世界,就会被他黏附在世界屏障之上的灵魂残骸,彻底吞噬。
这是他在虚拟世界中,操作命运线模拟过上千次后,试出的唯一解法。
唯一一个。
可以让温言喻。
活下去的命运线路。
也是唯一一个,牺牲最少,最为保险,胜算最大的方法。
付知言抬眸与傅寒川对视,一瞬间,敞开的灵魂与另一人共享出了这一信息。
所有计划在意识海中浮现,每一寸脉络都清晰可见,曾在世界帮助下,模拟出的无数条失败途径,也在其中。
傅寒川张了张嘴,想说些什么,可话到嘴边,却又觉得无比苍白。
苦涩又灼热的硫酸在体内打翻,在四肢横流,涌上心口,涌上唇齿。
恨不得将他原地腐蚀为一堆白骨。
安静的空间内,只有窗外细微雨声。
因此,楼梯口处忽然出现的脚步声,哪怕猛地停下也格外明显。
二人迅速回头看向楼梯口。
一头毛绒绒的白发在扶手处若隐若现,可见主人极力想要隐藏自已,但还是被脑袋暴露。
二人几乎是同时停止了呼吸。
又在意识到他们刚刚交流用的并非夏语而放松下来,从未有过的庆幸在心底闪过。
傅寒川喉结轻滚,咽下苦涩,收敛住汹涌的情绪,强行换上副正常的温和表情。
冲楼梯口处,试探性唤了声:“别藏了,我都看到兔兔的脑袋了。”
楼梯扶手处的白色毛茸茸僵了僵,迅速往下一缩,整个消失在了那里。
“是想玩捉迷藏吗?”傅寒川笑着问。
又是一声呼唤。
温言喻表情僵住,一点点从扶手后面探出脑袋,轻轻挥了挥手,解释道:“我刚醒……想下楼喝水,听到声音了,就过来看一下。”
“你们……在聊什么?”温言喻小心翼翼开口,生怕哪里说得不对让气氛变得更尴尬。
温言喻表情小心,半蹲在楼梯口,头发被睡的一团乱,身上只披着一件单薄的毛绒睡衣。
不敢上前。
看上去莫名可怜。
二人余光对视一眼。
生来就有的默契下。
付知言摆摆手,轻描淡写回道:“一些误会。”
“你们聊,我先去休息了。”随意落下最后一句话,付知言偏头,最后看了眼楼上少年,转身离开。
温言喻愣住,没明白。
傅寒川已经走上了楼,弯腰把人从地上拉起。
“怎么穿这么点就出来了,冷不冷。”
温言喻目光闪烁,微微摇头,“不冷。”
傅寒川按住温言喻的手,摸到一片冰凉,轻轻搓了搓,“手都要冻成冰了。”
南方的冬季比不上北方寒冷,几乎不会出现积雪的情况,但偶尔罕见的雨夹雪一下。
气温便会比平日降得更离谱。
风吹进走道。
“有点冷。”温言喻心虚的瑟缩了下,“你们聊了什么?”
傅寒川扯了扯唇,压下胸口几乎快要溢出的痛楚,佯装吃醋的微微偏头,低哼一声:“你是好奇我们聊了什么,还是在怕我欺负他。”
温言喻一愣,“什么啊!”???????
“我是……”温言喻顿住,不知道该怎么说。
傅寒川按住了他的后脑,将他往怀里一带,低头吻上了柔软的唇。
傅寒川吻的温柔,轻轻吮着他的唇瓣,淡淡的沉香气息混了点奇怪的苦味在舌尖缠绕。
温言喻迷迷糊糊。
原本还想要探究的心思被男人三言两语转开,一起回了温暖的被窝。
但。
着了凉的下场就是。
付知言唇线绷直,忍着火气,半蹲在药包前,不停往外翻药。
那个混蛋干了什么。
温言喻窝在沙发上,浑身上下被厚毛毯包裹得严严实实,脸被烧成了不正常的绯红,鬓发被不断渗出的冷汗浸湿,湿淋淋地贴在脖颈上。
接下了江婉柔的任务,楚星白拿着毛绒小兔,半蹲在沙发边,时不时用兔头扫扫温言喻的脸颊,让他保持清醒。
兢兢业业地反复提醒:“你现在可别睡,等会吃完饭了再睡,你可别睡,别睡,别睡。”
桑语担忧地坐在沙发另一边,看着江婉柔跑上跑下地找被子,拿枕头。
傅寒川端着热水从厨房出来,见到付知言翻出了其他药,出声提醒。
“红色盒子的言言早上才吃过,那药不能和普通退烧药混着吃。”
闻言,付知言停下动作,闭眼。
克制住火气。
没有当场把自已痛骂一顿。
[言言发烧了你不先给他吃退烧药,给他吃其他药,傅寒川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分不清先后级了。]
傅寒川皱眉反驳:[言言腰上的伤没好,现在断不了药,塑料盒子里那个是可以一起吃的退烧药。]
付知言一愣,[怎么可能还没好?我不是给……]
二人对视一眼。
傅寒川沉着眸子,目光示意摄影机和沙发。
付知言迅速闭了嘴。
【呜呜呜!宝宝!啊啊啊!垃圾地区!为什么要下雨!为什么要下雨!看把我家兔兔折磨成什么样了!】
【这哥俩昨天还吵架呢,今天就配合工作了,啧啧啧,求温言喻训狗教程。】
【求这哥俩不说E语教程,对我这个吃瓜人友好一点,谢谢。】
【不完全翻译,小狗哥说不爱哥脑子有问题。不爱哥说兔宝腰伤没好,断不了药。】
【呜呜呜妈妈的兔兔呜呜呜,我亲,我亲亲亲。】
听到二人的交谈声,温言喻抬了抬眼皮,朝付知言看去。
因为长时间的高温,头部上半圈火辣辣的刺痛,生理性的泪水不断流出,一双眸子水雾朦胧,眼睛周围肿了一小圈。
温言喻努力张口,想让这两个说人话。
自已听不懂。
可传达到几人耳中的。
只有沙哑到几近破碎的气音。
“乖宝,先不说话了。”江婉柔心疼得不行,不停抹着眼泪,“是不是饿了呀,小陆他们出去买吃的了,待会他们回来妈……就给你做饭。”
温言喻昏昏沉沉的做不出回应。
昨晚下了一整夜的小雨,虽然并未淋到身上,但本就不算温暖的气温骤降,南方的天也没有地暖,过道没有空调。
又是大半夜穿着睡衣偷听墙角,结果就是半夜就开始发烧。
傅寒川伸手探了下少年的额头。
还是烫。
温言喻紧咬着唇,除了难受下情不自禁发出的哼唧声外,说不出一句话来。
冷得浑身都在哆嗦。
“是不是很难受?”傅寒川皱眉问他:“还能坚持吗,不行我们就去医院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