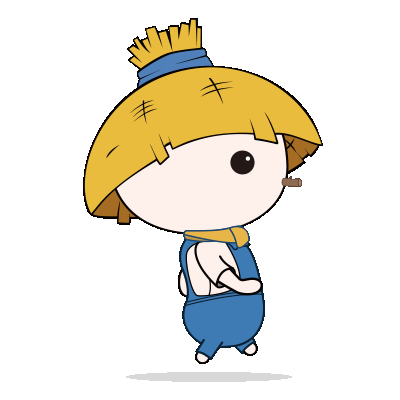“不要……我睡就是,别丢我出去,外面冷……以前有个冬夜,母妃将我丢到冷宫的院落中不准我进屋,我在屋外跪了半个时辰……脚上和手上都生疮流脓,很疼很疼……不过都过去了,今夜,谢谢帝师。”
云予薄静静听着,张了张嘴想要说些什么。
说什么呢?
安慰?她做不到,她只会沉默,况且,祁家的人,不值得她安慰,也不值得她同情。
祁昭浅说这些,又想要博取她的同情?
趁着云予薄胡思乱想的时间,祁昭浅慢慢松开云予薄的腰躺回了被子里,右手却一直抓着云予薄的袖子。
由于长时间抱着云予薄,她的腰也隐隐有些作痛,背上伤口也有些疼。
“帝师,在此,再次谢谢你。”
她轻声说着,看着云予薄的身影,慢慢闭上了眼。
云予薄就那么坐在那,没有回答她。
直到雨停了,不再打雷后,她给祁昭浅拉好了被子,起身离开。
推开门,夜风吹在身上,鸡皮疙瘩起了一身,屋檐还有雨水滴落下来,滴滴答答的声响不绝。
她看了看袖口上遗留的痕迹,想着刚刚祁昭浅熟睡的样子,垂下了眼眸。
宿命纠缠不休,云予薄头一次开始怀疑起了自已做的一切。
祁昭浅一夜到天明,她自知昨晚的举动不妥,大早上便敲响云予薄的房门,亲自端着平时放在书房里的戒尺来请罪。
云予薄打开门看见她时,眼中闪过一丝诧异。
祁昭浅身上的伤还未好,怎么那么一大早就过来找虐……
她忽略祁昭浅手中的戒尺,神色自若。
“大早上的,作甚?”
她问着祁昭浅,祁昭浅看了看她,“扑通”一声跪下。
她脸上带着害怕,身子挺的笔直却将头垂的很低,双手托举着戒尺,咬着唇开口。
“我来此认错。”
她说的认真,云予薄挑眉,伸手拿过戒尺,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变化,让人捉摸不透,猜不到她心中在想些什么。
祁昭浅说完便把手向前,做足了十全的准备。
“抬起头来。”
云予薄赫然开口,祁昭浅听见这话后心中一惊。
按道理,打手板心便好,要她抬头做什么……该不会要把戒尺打在她的脸上吧?
“不敢……”
她底气不足,只将手又往上伸了伸。
云予薄被气笑了,
她伸手将她抬起的那两只手打落下去,随后慢慢弯腰,左手擒住了祁昭浅的下巴,迫使她抬头。
“何错?”
云予薄明知故问,祁昭浅欲哭无泪。
“错在不顾帝师意愿,错在不知规矩,错在……帝师说放开之后仍不撒手……”
祁昭浅一桩桩一件件投入自已的罪行,这期间她满脑子都是要是被云予薄拿戒尺打脸,她也认了。
毕竟进一步的发展总归要付出一点代价。
四目相对,祁昭浅不自觉的抖了一下,她孱弱的身形倒映在那双漆黑的眼眸里。
云予薄冷笑一声。
“呵,你倒还记得挺清楚,你现在跟我说不敢?昨夜你胆子不是大的很?什么撒泼不要脸的法子都用上,现在却不敢了?祁昭浅,你可真行,大早上过来找打。”
云予薄冷声说着,祁昭浅咽了咽口水,还在想着说辞的时候,脸上传来轻微触感。
“啪——”
她猛的睁大眼睛,有些难以置信。
祁昭浅确实被打了,只不过她带来的戒尺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云予薄用擒着她下巴的手顺势便打了过去。
云予薄用了巧劲,声音很大,但是不疼。
祁昭浅愣愣的感受着,心底蔓延出一股难以言说的感觉。
云予薄变了,但是又好像没变。
若是以前,云予薄不可能只是那么轻飘飘的便别放过她,必然会使出十成的力气。
被她扇耳光,嘴角落血那是常事,甚至有几次耳鸣到什么都听不清楚,只有嘈杂声。
祁昭浅魔怔的抬手摸了摸脸,若不是云予薄的手还在她脸侧,她会觉得刚刚是错觉。
她想拉上那手,但终究不敢,只是捂着脸看云予薄,任由耳尖变得通红。
云予薄看着她震惊的样子觉得有些好玩,勾唇一笑,神色清冷,并无异样。
她收了手,直起腰后居高临下的看着祁昭浅,注意到了她通红的耳尖。
云予薄叹了一口气,恢复了往常的神态,把嘴角那丝笑意隐藏。
“滚,别碍我的眼,滚去书房将那日的罚抄写完,我一会儿过来检查,大早上扰人清净,可真有你的。”
祁昭浅早就注意到她嘴角的笑,自已也不由自主的笑起来,轻轻道:“是。”
她慢慢起身,恭敬的接过云予薄手中的戒尺,走回了书房。
此事便就此揭过,这其中的改变可不是一点半点,想必云予薄内心中并没有真正怪罪的意味,但她的骄傲和自尊,始终要碾祁昭浅一头。
祁昭浅早已意识到这一点……她笑着看云予薄,明白她是何意。
那日她觉得格外轻松,纵使前一日云予薄还在拿着话语像刀子一般往她心上戳,但今日,云予薄的改变让祁昭浅意识到自已的所作所为已经有了实质性的变化和发展。
而且,从那日她同云予薄说过之后,云予薄都未曾再让她去看谁家儿郎,也没让谁家儿郎来宫中陪她。
她心中有丝庆幸,可及笄礼越来越近,心又跟着提起来,难以放松。
昨日平常,她抄写完了那十几份,拿给了云予薄检查之后才休息。
云予薄看着上面的字迹,难得没有在骂她,而是点了点头,道出一句:“可以,去吃饭吧。”
祁昭浅笑着谢她,云予薄没有说话。
今日荼箐回宫,云予薄不在她身侧,祁昭浅摸懒又画了好几幅的画像。
看着眼前那些画像,祁昭浅忽然想到了什么,直接站了起来。
上次她绘画的那些画像还未收好,一直在柜子顶上!
趁着云予薄还没有回来,她寻思把那些连同这次绘画的一同转移到别地去。
她站了起来,踮着脚去摸柜子顶部,将那些纸张拿下来。